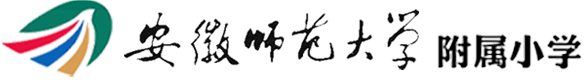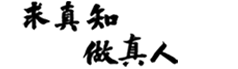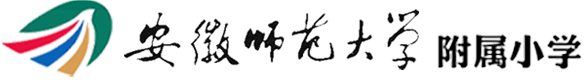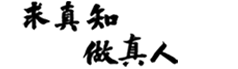为什么选名著?为什么出名著?
解读新课标阅读理念
个案剖析“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关键词释义:
*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在国家教育部2001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今年4月刚刚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以附录的形式做了“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和“关于优秀诗文推荐篇目的建议”,并对中小学生的阅读总量做了具体规定。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新课标“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中推荐的课外读物书目编辑出版,共49种。
背景
语文回到本来的位置
《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朝花夕拾》、《西游记》、《童年》、《论语》、《红楼梦》、《巴黎圣母院》、《哈姆莱特》、《西厢记》、《歌德谈话录》……在语文新课标“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中,我们看到一长串书名。每一个被这些经典作品滋养过身心的人都会相信,这些书名的背后,是一座座宝藏,藏在其中的宝物隔了成百上千年的岁月,依旧熠熠闪光。
有个美国人说,我们也许可以加快生活的步伐,但似乎无法改变达到生活目的所必由之路。他相信,在历史的各个时代,人类的基本问题都是相同的。凡是读过古希腊演说家德摩斯梯尼演讲集,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书简集,或培根和蒙田论文集的人,都不难发现,人们都在专心不懈地探索幸福和公正,美德和真理,甚至连其永恒性和变化性也在探索之中。因此,名著永远不会落后于时代。
一位教师呼吁,语文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必须抓住人文教育的核心。人文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震撼人的灵魂为出发点和归宿,使人热爱祖国,热爱生命,热爱人类,热爱大自然,使人得到一种更加真实、全面、深刻、有力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他认为,经典名著是实现这一切的最佳媒介。
新的课程标准根据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设计,将中小学生的阅读与鉴赏放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对阅读的数量、内容、质量以及速度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阅读推荐书目中,小学、初中、高中通盘考虑,互相衔接,其篇目大多为古今中外大家的作品。
经典名著对成长中的学生意味着什么?对我们这个时代意味着什么?2000年修订的语文教学大纲向学生推荐的课外读物包括初中10部、高中20部,这一规定在语文教育正逐渐走出长期以来工具性桎梏的当时,无疑是变革的一个响亮前奏,曾经令人兴奋不已。新课标则规定了对学生阅读量的要求,推荐的课外读物书目也从修订大纲的30部增加到50余部之多。从中不难看出新课标中新的阅读观的彰显。
个案
人文社打“人文牌”
作为一家专业的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比较早地捕捉到普通教育语文课程改革中对人文教育的关注这一信息。3年前,当新修订的语文教学大纲颁布,其中明确列出30部文学名著作为“课外阅读”推荐书目的时候,人文社以其灵敏的“嗅觉”和版权固有的优势出版了“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获得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动起一轮阅读经典名著的热潮。
随着今年4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的颁布,人文社又在第一时间推出了“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该书策划者李明生认为,新的语文课程标准重视对中小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提倡阅读,背后有两个概念在支撑:一是新课标提出,语文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二是从2000年的语文“新大纲”开始,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因子在不断加大。作为以出版人文类书籍见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关注语文教学改革的进程,为学生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大餐本是题中应有之义。
由于人文社享有《骆驼祥子》、《繁星·春水》、《女神》、《子夜》、《家》、《雷雨》、《茶馆》等作品的国内专有出版权,所以对新课标推荐书目而言,这套丛书相对比较完整和全面。而《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均以最早或最为通行的刻本为底本,校点、注释基本汇集了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朝花夕拾》、《呐喊》选自获国家图书荣誉奖的《鲁迅全集》,由著名专家教授校注,称得上国内的权威版本。这套书中的一些外国作品因翻译的精准而使经典性更为突出,如杨绛先生译的《堂·吉诃德》曾获西班牙国王颁发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朱生豪先生译的《哈姆莱特》在中国文坛和剧坛历经半个多世纪,译文之精妙至今无与匹敌。
为帮助学生自读,便于教师讲解,配合这套书的出版,人文社还即将推出《课外文学名著导读》(分小学、初中版和高中版)。
诞生于语文课程改革背景下的“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在一定程度上传递了一种新的阅读理念。这种理念的核心是什么?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郑国民进行了解读。
解读
少做题 多读书 读好书
记者:9年,405万字。在语文新课标中,我们看到对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做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这样的规定出于何种考虑?它与学生学习语文基础知识有何关联?
郑国民:语文教育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讲解、记忆规律性知识,注重概念的掌握及其精确程度,必然削减、忽视学生的语文实践。忽视语文实践的结果是使学生的语文积累更为薄弱,无法真正对这些规律或概念进行理解或运用。所学的内容是干瘪的,缺乏生命力的。让这些规律性、概念性的知识充满生命力本身就需要一定的“基础”,这个基础是根植于语文实践活动过程中,经过不断体验而发现的规律,富有“生成”的活力。从这个方面而言,语文学习必须有一定的积累,积累的内容包括语言材料、文章样式、思想感情、生活体验。具备了一定的积累,才能通过一定的引导从似乎是无序的现象中发现有序的规律。其中阅读是语文积累的有效途径。
记者:新课标推荐书目制定的依据是什么?
郑国民: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各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来看,很多国家在母语教育中都在增强民族文化的教育。例如日本的基础教育以增加学习汉字的数量为切入点来加强民族文化教育,试图走出培养“洋魂洋材”的教育泥淖。英国母语教育注重本国经典名著的阅读,7—11年级的阅读内容大多是名家名篇,例如要求学生阅读两部莎士比亚的戏剧,阅读1000年以前两位重要作家的小说和四位重要诗人的作品等等。由此看出不同国家的母语教育都在传承、发展着不同国家的文化。
语文新课标总目标要求,“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让学生在认识和体会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同时,从民族文化中获得创造的智慧。另外,能够尊重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多种多样的文化,并借鉴吸收这些文化的精华。这样的课程目标要充分体现在课程内容和课程实施过程中,阅读经典名著、背诵优秀诗文是贯彻、落实课程目标的途径之一。
记者:为什么向中小学生推荐经典名著?
郑国民:强调阅读经典名著、诵读优秀诗文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由于阅读活动在现代社会存在着严重危机。现代科技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立体、多感官的享受,人们已经习惯于坐在电视机等声像俱全的媒体面前,而不太情愿坐下来读一本书。即使读书,很大一部分人进行的也是一种“快餐式”的阅读。这已成为大众阅读活动的主流,并且在学校广泛地散播着。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平庸化阅读掩盖了对阅读内容的敏感与批判,在一定程度上,阅读并没有给学生带来对社会和人生的严肃而深刻的思考,没有产生、引发对自我、外面世界思考的动力。同时,这种公式化、自动化的阅读活动也钝化了学生表达的锋芒,失去了富有个人色彩的、精确而多样化的表达能力,无法表现学生精神世界的多样性,以及对世界认识的多样化。我一直认为,如果一个人在学生时代没有经历阅读经典作品的“洗礼”而离开了学校,不仅会给人生带来缺憾,而且很难抵御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和诱惑,也无法充满自信地吸收来自不同背景文化的精华。
记者:经典名著是经过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的优秀作品,但由于其产生的年代久远,和当代生活的距离会不会导致学生接受上的困难?在这方面,学校应以什么样的角色引导学生进行经典阅读?
郑国民:虽然从时间上来说,这些作品产生的年代与现实有一定距离,但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就在于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社会、自然和人生的典型性认识,典型意味着具有普适性意义的内容。因此,这些作品本身洋溢着一定的亲和力,不会因时代的距离而隔膜,而会不断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也正因如此,对这些作品的理解是永无止境的,会随着读者阅历的丰富而不断发展,任何人、任何时代的理解都只能是相对的。常读常新是这些作品独特的品质,不必要求一步到位,实际也是到不了位的。孩提时代是一种理解,青年时代是一种理解,老年也许又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意味着不同的境界。如果把成年人对作品的理解强加给孩子,或者期望孩子能够有成年人那样的理解都是错位的追求,结果只会引起学生对读书失去兴趣。对话理论认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平等对话的过程。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但在阅读过程中,教师的作用并非被否定,而是得以重建,成为“内在于情境的领导者,而非外在的专制者”。
记者:新课标明确提出: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鼓励学生自主选择阅读材料。总的来看,这种阅读理念体现了什么样的教改精神?
郑国民:对学生在阅读方面的要求的变化意味着语文教育观念的转变。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课程价值取向的转变。在文化多元化急剧演变的现代社会背景下,语文教育如何面对严酷的现实,使学生能够站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具有足够的自信心和独立性,在文化扩张或冲击中得以创造性地发展,这是重新建构语文课程价值的重要任务。
记者:据我所知,您是北师大版《小学语文》的主编之一。作为专家,您如何看待“大”学者“写”小文章?
郑国民:应该说,专家学者为中小学生编教材在我国是有传统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陶行知等都编过小学教材,著名学者林纾也曾编过中学语文教材。但近几十年来这样的事似乎越来越少了,甚至在高等院校逐渐形成了为中小学做事低人一等的悲哀局面。实际上给孩子编书的难度决不低于一些研究项目,也许这不算学问的工作比做学问还难些。没有一流水平的教材编写者,没有大学者的视野,指望出现一流的教材和读物是不现实的。我建议专家学者都来关心中小学语文教育,为孩子们编写一流水平的教材,编创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学生的发展价值最大的课外读物。因为这不仅是语文课程改革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学者的责任。
《中国教育报》2003年7月3日第5版
|